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劉虹韡
指導教授:梁秋虹
當人權以美術之姿現身,在1994年人權海報大展中、在2006年迄今的綠島人權藝術季中,也在人權畫家與人權畫作中。幾項標語如伸張人權、控訴不義、記憶保存,反覆地出現在各式文本,但當筆者試圖解釋「人權美術」時,卻發現這個新字詞尚未有完整的論述與發展史。
本文欲釐清「人權美術」字詞的本質,並了解人權美術在何種社會脈絡下誕生,這當中又經歷了哪些波折。於是第二章「從人道到人權——尋找臺灣美術史中的人權美術」,將檢視臺灣美術史著作,查找人權美術是否入史;而不同面貌的人權美術對應不同的社會背景,因此第三章「政策與法律中的圖畫限制」將探討戒嚴時期人權美術與政治權力的關聯。最後,第四章「解嚴前人權美術的再挖掘」,意圖突破戒嚴時期創作的限制,挖掘隱性的人權美術。
在臺灣美術史論述中,美術史家共同指出一位日治時期便開始創作的前輩畫家具備著「人道精神」——洪瑞麟。洪瑞麟曾描繪在大雪中辛勤生活的日本山形縣居民身影,也畫下臺灣底層家庭生活場景;1938年進入礦坑工作後畫下的礦工畫,更是成為他的系列代表作。不若洪瑞麟展現對於弱勢族群的直接關懷,日治時期的時局色與地方色畫作則是隱晦地展現了畫家受社會與土地牽動的情感,而這份關懷也延續到了戰後,成為美術史家所稱時局色的延續,又或是社會寫實的開展。
戰後另一更為直觀的案例為「木刻版畫」:黃榮燦的《恐怖的檢查》、荒煙的《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朱鳴岡的《迫害》等,具備著見證與批判歷史事件的特色。於是時局畫、社會寫實畫作,以及木刻版畫,成為美術史家筆下戰後初期的時代見證者。
然而在戒嚴時期,這些試圖與社會連結的畫作消失了,美術史家與畫家將原因指向陳澄波與黃榮燦的逝世,以及戒嚴時期畫作的被審查與禁忌。於是本文試圖自政策與法律,為畫作的消失尋得確切來源。
執政者對文藝的限制,並非僅是看似遠在天邊的反共宣言,這些宣言向下延續到了政策、展覽會、文藝團體,與媒體中。例如,之於畫家,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與畫家的發展息息相關,但歷屆簡章中編列「有違反國策之意識者」以及「有違法善良風俗者」不予展覽,即是條限制畫家創作題材的意識規範。
除了政策,法律更是以刑罰作為限制的手段。什麼樣的圖畫不能畫?畫了會有什麼懲罰?是否有法律依據與判決案例?本文以政府公報資訊網以及全國法規資料庫作為法律資料來源,發現戰後臺灣的歷史上,以圖畫為叛國宣傳,或是以圖畫洩露軍事機密等,為主要限制標的。而自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史料資訊系統中的補償金申請案、臺灣轉型資料庫內的決策資料,以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中的檔案中,可見實際因圖畫被判刑的案例。繪製共匪符號、塗鴉元首畫像,又或是畫作隱含落井下石政府處境之意,皆成為被判刑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戒嚴時期,規範著不得以圖畫洩露軍事機密之法律,並非僅是軍人適用,觸犯〈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妨害軍機治罪條例〉者交由特種刑事法庭,而觸犯〈懲治叛亂條例〉者也會交由軍事機關審判。
這些政策與法律的存在,限制了試圖「叛國」的圖畫,更使畫家對於創作規範感到戒慎恐懼,最終難以踏出相對安全的區域作畫。但這並非代表戒嚴時期便毫無人權美術存在的可能。為了尋得美術史論述之外,更多隱晦人權美術歷史節點,四個場域成為本文的研究標的:漫畫、美術期刊、境外之地,與黨外雜誌。
在漫畫場域,《新新》雜誌短暫存在於1945年至1947年,其中收錄的漫畫表達著對日本戰敗的揶揄,還有對貧富不均、通貨膨脹的直接抨擊,開創戰後初期以漫畫針砭時事的先河。在美術期刊場域,《雄獅美術》始於1971年,終於1996年,跨越了戒嚴與解嚴,雖以推廣鄉土運動為名,卻是蘊含了大量的人權意識,在天安門事件藝術聲援運動中、在各式人權相關展覽的介紹中,更是在代理畫家劉耿一的畫作與文章中。
另外,既然1970年代臺灣對內的經濟衝擊,和對外的外交挫折促成鄉土運動,那麼除了境內的《雄獅美術》,境外之地第一線感受到國際情勢的畫家又會有何種回應?旅外畫家侯錦郎在臺灣師範大學求學時期所作的《心在凍原之人》暗喻著白色恐怖時期的壓抑,《奔》則是描繪原子彈爆炸時日本人民的逃亡景色。而在他為了學術研究前往法國打拚之時,卻持續地參加歐洲臺灣獨立聯盟,並投稿研究於政治傾向明顯的刊物,甚至是救援境外受政治壓迫的臺灣人。解嚴後,他更是畫下《反核四的抗爭》與《民主殿堂——弱勢者的抗議》這類直觀描繪臺灣社會運動與政治情勢的畫作。即使身處境外,侯錦郎從未停止關懷臺灣。
時間拉至解嚴前夕,在黨外雜誌場域中,竟在書封見到畫家吳耀忠的畫作。吳耀忠秉持著追求現實理念的決心,在黨外雜誌的書封描繪著人民勞動的場景,而他加入這個與查禁相連的爭議性場域,更是畫家不畏時代限制而涉險的例證。
見於現代的「人權美術」一詞,其實早已經以「人道」、「現實關懷」、「社會批判」等樣貌現身於臺灣美術史論述中,但是因人權概念的匱乏,加之戰後戒嚴時期的圖畫限制,人權美術長年沒有它的名字,也無法成為美術界的主流,但這不代表它在歷史上曾經缺席。筆者聚焦於美術史研究中邊緣化的四個場域,漫畫、美術期刊、境外之地,與黨外雜誌,發現人權美術跨越了戒嚴與解嚴,它並未消失於戰後臺灣美術史,而是伴隨著情境有不同程度地表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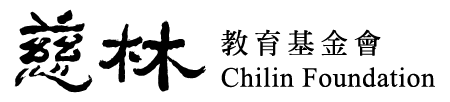

 捐助慈林
捐助慈林
 全球先進SSL 256bit傳輸加密機制
全球先進SSL 256bit傳輸加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