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所博士生 呂東熹
指導教授:林巾力
臺灣現代報業的發展,始於1895年日本統治時期,報刊的引進與語言及教育環境的有很大的關係。
日本統治之前,臺灣是一個漢文與書房教育的社會,統治者經由漢文識字圈(或稱漢字文化圈)的共同經驗,透過現代化大眾報刊的引進,收攬了前統治者(清治時期)原本的社會領導階層,尤其是期待科舉考試取得晉身管道,卻因改朝換代而破滅的傳統文人,在日本報刊「漢文欄」的吸引下,以「漢文記者」的身分成為新興領導階層,同時也自我塑造為歷代「史官」的角色。
緊接著,日本也引進現代化的新式教育,而產生另一批跨語言的殖民地青年,尤其是具留學日本的知識青年,他們利用殖民地教育所學習的雙語讀寫能力,積極地善用、引進近代文明的知識,創辦報刊,傳播理念與台灣人意識。
《近代台灣新聞記者的社會實踐(1897-1947)》,是以記者職業為研究主體,原因主要有兩點:1.記者是日治時期台灣的新興職業;2.從事記者工作者屬於社會領導階層,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對象與範圍,主要是以日治時期傳統舊文人知識社群,以及新式教育下的知識份子,如何投入日本所引進的現代化報刊,成為新興職業──新聞記者的一分子。但不管是傳統舊文人,或新式教育下的新興知識分子,他們在面對日本帶進臺灣,具隱藏性的「同化」政策,他們各有不同的應對之道。
一、傳統文人記者的跨界與摸索
立身於現代報刊的傳統文人,從漢文欄記者、主筆政,逐漸體認到「史官」與「新聞記事」的想像有相當的差距,但在報刊漢文欄的傳播影響力下,傳統文人,特別是具「詩社」背景的文人,以跨語言漢文記者的身分,透過吟詠與新統治者之間,慢慢找尋到與祖國文化契合的互動橋樑。
當然,現代性的「記者」職業,雖未完全在傳統文人身上,形成專業認知的建立,但經由官方媒體「新聞記事」的實質體驗,其對「記者」的認識,已經超越了對「史官」本質的期許。不過,隨著總督府統治日漸穩固,舊時代傳統文人「學而優則仕」的傳承,已在「記者」這個新職業的建立下,成為新文明的象徵。
儘管有部分傳統漢文記者,橫跨了新式教育下進入報刊的新一代「記者」群,但傳統文人出身的漢文記者,其認同原型仍然存在,在漢詩吟詠、文言小說的創作上,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二、新世代臺灣人記者的跨界與抗爭
臺灣與中國報業之間,有著相似的經驗軌道,除了洋人引進的傳教報刊外,中、臺兩地的報人都與留日經驗有關,1920年代之後,臺灣新一代知識分子,在島內接受殖民政府另一個現代性的教育制度,進而前往日本的青年留學生,近距離吸收了現代報刊在政論上的影響力,亟思透過創辦報刊,來表達對殖民政府的不滿或爭取權利,「文人報業」於焉產生,與日治初期傳統文人在漢文欄的表現截然不同,臺灣青年留日學生與島內治政、社會運動結合,針對殖民府的批判、建言,成為新一代「記者」(或「編輯」群)的使命。
「文人報業」時代,報刊無法直接在島內印刷發行,1930年代之後,報刊移到島內,甚至進一步創辦日刊,新世代知識分子進入現代化報刊之後,運動路線背景強勢的「記者」,以及專業意識取向的「記者」,彼此之間有了周旋與論辯。
這樣的論辯,讓新一代知識分子在報刊上百家齊鳴,從右翼到左翼,從親日到回歸祖國的臺灣青年,紛紛樹立了同人性格強烈的言論地盤,在政論、在文學上各抒己見,當然也有一部分走向趣味、遊藝的「小新聞」路線,同時為臺灣「新聞業」與「記者」職業的言論市場,編織了繽紛奔放的時代印記。
不管是運動路線或專業意識的臺灣新聞記者們,抑或是左翼、右翼青年的政論報刊,都積極想在言論表現上,為島內的自由進步貢獻己力。這樣的精神與理想,延續至戰後,並且成為戰後各領域的菁英。
特別是新興知識分子,都同時扮演著「有機知識份子」與「文化中介人」的雙重角色,他們不但成為文化與信息傳播者,也介入政治,亟思改革社會實踐理念。但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台灣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最先是取消漢文欄,緊接著,緊縮言論,臺灣唯一的喉舌《臺灣新民報》不得不更名《興南新聞》,這樣的時局,如同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書寫意識,在現實政治現狀之下,臺灣人記者,遊走兩岸不同勢力與政權,周旋於臺灣人媒體、抗日報刊、親日媒體,體驗了做為孤兒無奈的情境,待至六報合一成《臺灣新報》,言論自由已成一言堂。
三、戰後噤聲失語的臺灣媒體人
這批日治時期的新興知識份子,在抵抗日本殖民運動過程中所建立的「市民社會」意識的新聞記者,隨著日本戰敗,新聞魂再次甦醒,紛紛投入報業戰場,接續戰前評論時事、關心國族問題的使命感,企盼一展新聞長才與言論改造社會的願望,豈料一場1947年「二二八」巨變,日治時期培養的臺灣人記者,被殺、或被捕、或逃亡,一整個世代記者幾乎全部退出新聞舞台,臺灣人
因而成為被噤聲的一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台文所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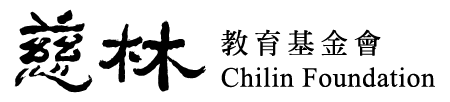

 捐助慈林
捐助慈林
 全球先進SSL 256bit傳輸加密機制
全球先進SSL 256bit傳輸加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