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宇雯攝
我想,我是那顆叫做「審議民主」的種子。
「要在營隊與課程的框架中,運用審議民主串接,促進大家反思並產出行動。」接下營隊主持人這份任務的時候,我其實是非常惶恐的,這是我第一次在審議模式的框架外,將它的概念與精神鑲嵌在其他形式的活動中。
營隊在運作上經常是大量的團體行動,甚至延續著威權時期救國團式的營隊文化,台灣舉辦的營隊活動中仍然存在許多生活規範、樹立權威或建立集體感的活動,然而,審議民主講求多元的參與、資訊對等的討論,藉由相互理解和溝通,尋求民主社會中的共同意見,即便我知道如何在一般的會議中實踐審議目標,但要在「營隊為主,審議為輔」的條件上運作,就算準備好簡報、規劃好議程,但直到活動開始前,我都還不是很有把握能扮演好主持人的角色。
我在營隊開始前的心情,更像是報名參與的學員,想到營期課程豐富又難得的講師陣容,還能與在各地投入不同公共議題的青年夥伴交流,更是終於有機會走訪慈林,參觀台灣民主運動館、紀念館與各種歷史、藝文典藏,光是這些就讓我期待不已,而有機會將自己所學的審議知識與技術運用在不一樣的場域,更是讓我躍躍欲試。
拓荒的人、成長的苗、綿密的林。
有趣的是,在營隊第二天下午,我決定大幅度調整原先規劃的議程。原本設計中有設定主題方向與每日議程,讓青年循著規劃一步一步地進行分組討論,然而,由於課程緊湊,僅有的休息時間大家沒有心力討論報告,用餐時間輕鬆的聊天交流反倒十分熱絡。於是,順著大家當下有限的能量,我捨棄原先的主題與議程,改用開放空間(open space)的審議模式,讓青年不受限制的提出想與其他夥伴交流的議題,大家也能自由地選擇想參與的討論。對我而言,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實作經驗,臨時的修改審議流程、自己組織一場open space,更是增進自己在判斷團體動力上的自信。
在書寫文章的此時,回想起這段意料之外的環節,我隱隱約約地,看見台灣民主化的成果正在茁壯。在這樣的議程轉變中,大家從聽課、學習的學員,轉變成提問、倡議的青年主體;從被動接受議程的參與者,成為主動開創議題的主持人。議題發展空間也從聚焦在五個社會議題面向,變成更加百花齊放、問題導向的創意思考,而我也從掌握議程設計權力、承擔成果壓力的規劃者,變成釋出更多的空間與彈性讓青年自由發揮的協助者。
調整後的討論相當精彩,來自馬祖的夥伴探討如何與立場不同的人對話、影像與教育工作者大談推廣人權議題的想像,也有還是學生的青年夥伴試圖將國防、族群議題帶入校園。我想,這樣的動能轉變不僅僅是我個人或者制度變化的功勞,也是建立在主辦單位和班主任對學員的信任之上,更是奠基在學員擁有獨立思考、批判、表達、自主行動的能力上,才能有如此豐富的產出。民主運動的前輩們,扛著鋤頭、一次次地翻動威權體制下貧瘠的土壤,所種下民主的種子,現今已經茁壯成涵融多元個體、抵禦台灣與國際社會中風風雨雨的根莖與枝枒。
「再繼續深根茁壯吧!」
在營隊的最後,我運用諮商牌卡讓大家分享了各自想說的話。
「我選的這張牌上有很多綠葉...,這是我第一次在實體見面的場合見到這麼多的同溫層。」
「我本來很擔心自己年紀太小,但是大家不分年齡,都很願意聽聽我的想法,幫助我把想法變得更好…。」
「...一朵花盛開是只有一個人的豐盛,但我後來選擇這張牌卡,是因為很多顆心更像是大家一起的感動。」
我猜想,也許不是所有人都在這個「感性時刻」深受感動。回想十八歲時的自己,在營隊結束時總會情感充沛、倍受感動,但隨著年紀的增長,時間和經歷也讓心中感動變得有些複雜,不論是慈林青年營,還是我過去參加過的每一場審議討論,我相信不只是我,願意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們都是對台灣的未來還懷抱著期待,而我也經常捫心自問「活動結束了,然後呢?」。可是事實上,回到日常生活,我也會有不想關心時事的時候,我還是要面對遲遲沒寫完的論文,和我不得不承認的懶惰與消極面。雖然在心情分享的階段大家總開玩笑地對彼此說「不要哭」,當下的我卻異常理性的覺得,自己並不會哭,那是知道要實踐社會行動從來就不是十分鐘報告如此簡單,也是知道四天營隊高談闊論的合作也不見得有緣份能持續。
可是營隊結束那天的晚餐時間,眾人在林義雄先生老家上方看見一道彩虹。物理上,彩虹跟青年營一點關係也沒有,過了今天,世界還是一樣運轉、社會也還有許多不公不義,也許有些人在營隊結束之後就再也不會見面,也許我們仍然無法不把人權的價值、台灣的命運扛在肩上。可是那道彩虹和蘭陽平原的景色,卻讓我感受到很純粹的美好與希望,也許只是我投射了自己心底的直覺,藉著彩虹,彷彿是林老太太、亮均姊姊、亭均姊姊在天上微笑地說「即便沒有然後也沒關係,光是這幾天知識、想法、人與人之間的相聚,就足以成為彼此為台灣的民主與社會繼續往前走的養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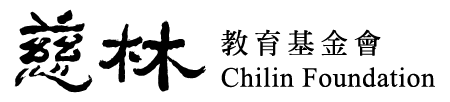

 捐助慈林
捐助慈林
 全球先進SSL 256bit傳輸加密機制
全球先進SSL 256bit傳輸加密機制